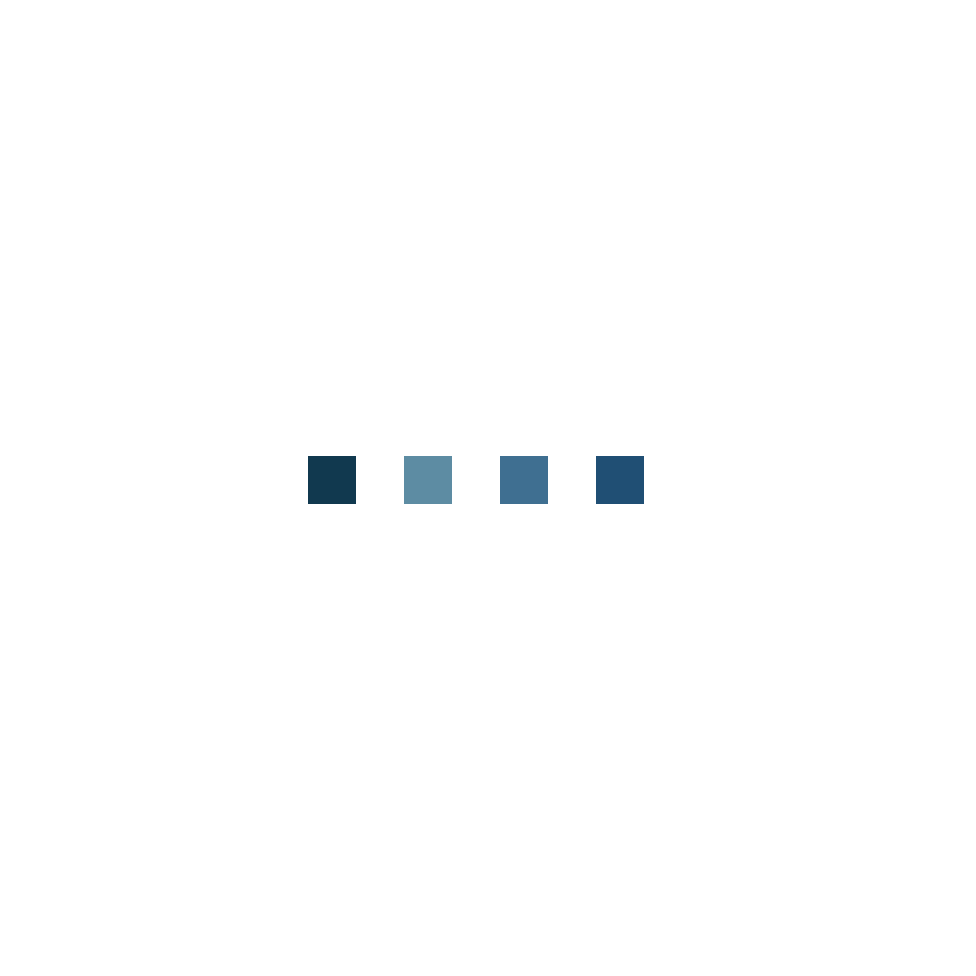洪耀南/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、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
近年來,中國社會上流傳著一句頗為辛辣的話——「不是我需要社保,而是社保需要我」。乍聽像是一句調侃,卻直指制度深層的焦慮:今天的社保,更像是在為自身續命,而非為繳費者築起可靠的安全網。
自2019年起,社保徵繳權從經辦部門移交至稅務系統,並配合司法對「不繳無效」的明確判例,徹底堵死了自願參保的空間。到2025年,北京靈活就業人群的最低養老保費已高達每月716元,對於月入僅數千元的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而言,這筆費用不只是沉重的經濟負擔,更是一種被強制抽走收入的剝奪感。官方宣傳口中的「保障未來」,在現實中更像是為財政尋找穩定的現金來源。在中小企業和靈活用工領域,這樣的強徵直接壓縮了勞動者的生存空間,也推動了用工市場的內卷化與機械替代。
更大的背景是,中國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——老年撫養比攀升至22.5%,平均不到五名勞動者就要供養一名老人。每年新增退休人口超過兩千萬,而勞動力則以每年三百至五百萬的速度縮減。2024年社保基金帳面雖有餘額,但背後是高達2.6兆元的財政補貼在硬撐。這一切意味著,制度對年輕人的依賴已經遠大於年輕人對制度的依賴——一旦繳費人數下滑,現金流便立刻告急。社保已不再只是公共保障,更像是一種長期徵收的「人口稅」。
靈活就業群體的處境尤為尷尬。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以靈活就業為生(官方統計口徑中,每週工作一小時便不算失業),但只有三分之一享有完整的「五險」。收入的不穩定、繳費與待遇轉接的困難、對制度的低信任,使他們本就疏離於社保體系之外。如今的高額強制徵收,反而促使許多人選擇「脫制度化」——不報稅、不簽合同、轉向灰色經濟。結果是,制度為了擴大基數而拉人入局,卻因成本過高而逼走更多人,陷入自我消耗的惡性循環。
更致命的是信任缺口。中國審計報告顯示,至少有十三個省份挪用了超過四百億元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,用於填補地方財政赤字或支付公務員工資。這不僅削弱了基金的長期償付能力,也在公眾心中埋下了不信任的種子。歷史上的上海「陳良宇案」等高層腐敗,早已證明風險並非空穴來風。當年輕人意識到「我的錢不是在等我退休,而是在替別人填坑」時,社會契約的根基便迅速鬆動——在不少人眼中,社保已從「養我安度晚年」變成「我養它活下去」。

經濟增速放緩、財政壓力上升、人口紅利消失,使得社保制度的邏輯徹底反轉:它的首要目標,不再是保障個人未來,而是確保系統本身不斷裂的現金流。這正是「社保需要中國人民」這句話的真義——制度的存續依賴於每一位繳費者的即時供養,而非長期互信互惠的契約。
2025年9月1日起,《勞動爭議司法解釋(二)》正式實施,明確所有「不繳社保」的協議一律無效,勞動者可據此解除合同並獲得補償。這使得企業逃避社保的法律風險驟然升高,外包掛靠等規避方式也可能被追責。對企業而言,五險一金成本可達薪資的三到四成,是沉重的負擔;對勞動者而言,高繳費與低信任並存,參保意願依然不高。制度因此陷入兩難:執行越嚴,流失越多;放鬆執行,現金流危機則加劇。
如果要擺脫「人養制度」的單向依賴,就必須降低繳費門檻,推行非捆綁式與差異化繳費,全國統一(跨省有效)讓低收入群體不再被排斥;同時提高透明度,公開基金的收支與投資,建立可追溯的責任機制;更要明確優先順序,確保基本醫療與最低養老優先,避免「空頭支票」式的福利膨脹。
真正的社保,應該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互助契約,而不是一場現金流的生死拉鋸戰。當制度的延續需要不斷汲取年輕人和靈活就業者的收入時,它就已經偏離了本旨。要讓「社保需要中國人民」不再成為現實的諷刺,唯一的辦法,就是讓它回到初衷——保障人的尊嚴與安全,而不是讓人淪為制度續命的燃料。
★《鏡報》徵文/《鏡報》歡迎各界投書,來文請寄至:editor@mirrordaily.news,並請附上真實姓名(使用筆名請另外註明),職稱與聯絡電話。來文48小時內若未收到刊登通知,請另投他處。回到原文
更多鏡報報導
CSIS兵推懶人包 揭示台灣如何反制中國對台海封鎖戰法
王丹專欄:中國是一個佈滿「情緒地雷」的社會
比亞迪將進軍台灣市場?陸委會:會針對中國品牌車高度審查